木心: 我们的国民性
伟大的宝塔,旁边没有别的宝塔。……斯宾诺莎、达·芬奇、亚里士多德,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。也有一群人,成就文学艺术上的时代星座——请注意用词,我不用“流派”。星星是发光的,每个艺术家已经是星星了,同样能光辉灿烂,照亮时代。
靠宗教,靠政治,都不能拯救人性,倒是只有文学和艺术。
索性讲纪德。他的名言:“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。”……我记住这句话时,十七八岁,一辈子受用不尽。……五十年来,我的体会:人性中最大的可能,是艺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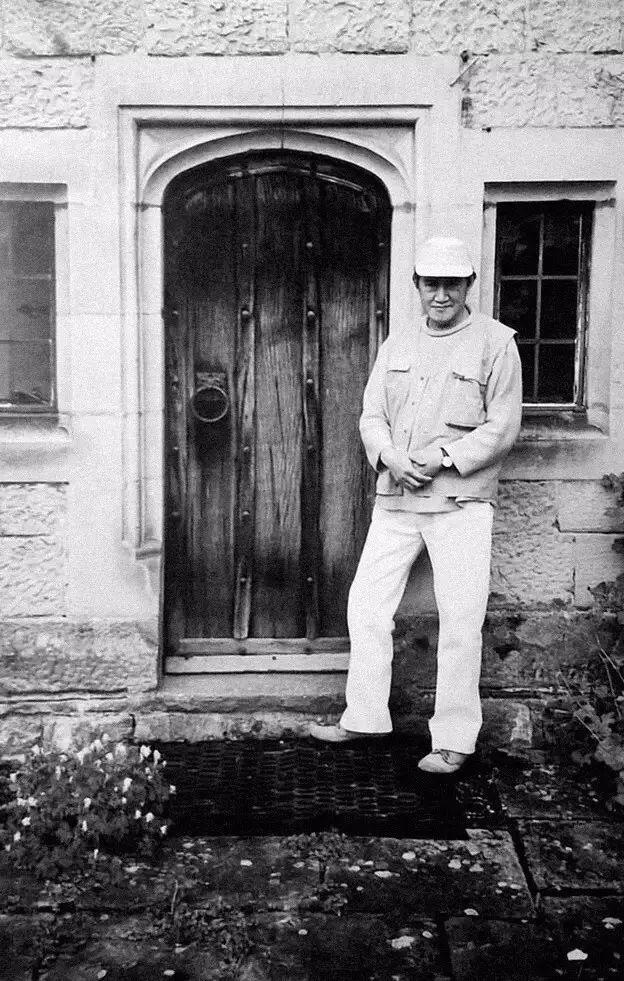
现代艺术一味否定传统,没出息。如果你是强者,为什么要否定传统?越新,越脆弱。总要反前面的东西,毁掉。真的强者,自己往前走。
荒诞派主要几个作家,都很有修养才华……但我觉得荒诞派这些作家,矫揉做作。我在一首诗中说,现代的智者,都是自己要假装自杀,要世界作陪葬。这些批评家、观者,都是假装要殉葬,作者呢,假装要自杀——都没有死。
这就构成现代艺术的景观,他们在舞台上把世界写得一片黑暗,他们自己生活得很好——这里有欺骗性。
宇宙无所谓荒谬。人在里面,觉得荒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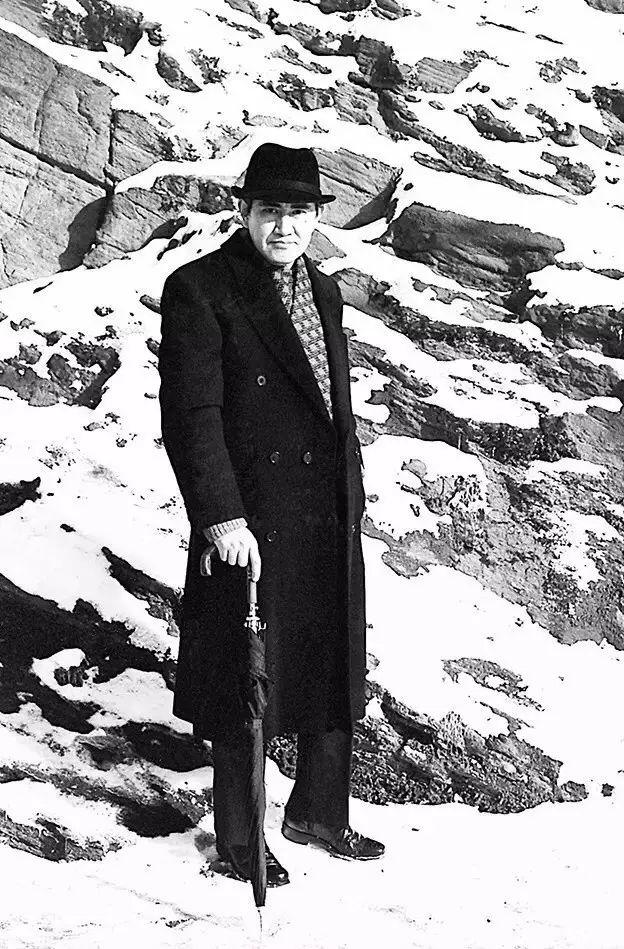
科学家,以身殉道,是真正的绝望。文学家的绝望,是假绝望。有人讽刺过叔本华,说他写悲观哲学,自己活得很好。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。新小说派,失落的一代,迷茫的一代,说穿了,是“智者的自忧”,夸大了世界的荒谬。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,还是病人多?在他们的作品里,全是病房,病人。
我常常想起莫扎特。他的意思,是人生嘛苦,艺术嘛甜。他们呢,人生苦,艺术更苦。给你一杯苦水,要你喝,还问你苦不苦。你说苦,他高兴。

这是一个骗子骗骗子的时代,嫖客嫖嫖客的时代。文艺女神早就飞走了。我是不是言过其实呢?没有。实际上还要厉害。
文学是人学……一流的艺术家,叫他做件事,他做成艺术品。“垮掉的一代”,发生在五十年代……以我看,其实是大战的后遗症,是人性崩溃的普遍现象。是外向的社会性的流氓行为,内向的自我性的流氓行为的并发症,既破坏社会,又残害自己。
主要是文学青年。他们对既成的文明深恶痛绝,新的文明又没有,广义上的没有家教,胡乱反抗……这一代其实不是“垮”,是“颓废”,是十九世纪的颓废的再颓废。

一个东西,不要看他们说些什么,要看他们做得怎么样……一句话,他们追求的不是理想,而是追求生物学上的人的解放……他们要取消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——不是与传统的界限。他们暗中说,或者明讲:他们的祖师爷是惠特曼。但惠特曼是清醒的。他们不清醒。在生活上、艺术上,他们是双重的短命。其中有个人(杰克·凯鲁亚克),有出息的……到四十七岁,写了十来部小说,最后回到现实主义。
看来,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出路。
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。我小时候写作,环境、天气,都写好了,咖啡也泡好了,主角开口了——完了,不知道写什么对话呀。

文学家应该生龙活虎。
附带讲,通常都有这规律:画家、艺术家,都有准备期,准备期越长,高峰期越高。准备期有两种:一是不动手,光是“生活”;一是动手,动手的准备期。
打工,其实是为了接触人,看人。洗五十年盘子,不识人,什么也没用,只识盘子——这叫做知人之明,知己之明。知人,知己,缺一不可。

生命的悲哀是衰老、死亡,在这之前,谁也别瞧不起谁。诸位要有后劲,后劲就是出路。怎么说呢?就是孟子的话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这股气要用到艺术上,不可败泄在生活上——不要在乎苍蝇、跳蚤、蟑螂,不必义愤填膺。一天到晚谈苍蝇、跳蚤、蟑螂,谈多了,会像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那样,自己也变成苍蝇——这就是我所谓的“初步成功。”肥鸭在烤箱里转呀转,油光光的,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。
现在,在街上,还能看到垮掉一代的“遗腹子”,背着包,到处旅行。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,滥用自由。要说他们是革命,探索,谈不上。想颠覆,想破坏,可贵的是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。但是吸毒,乱交,是用恶来反对另外一种恶。我看是含不了多少恶意的愚蠢。到头来是吸毒,堕落,潦倒街头。

在这里,不论各位是为了吃饭艺术,还是为了艺术吃饭,但有饭吃,可以谈艺术。
诗,是高贵。
中国的酒、茶,很近于诗的本质。好酒、好茶,都有特质、品性,好酒不能掺一点点水,好茶不能有一点点油腻。这品性,是上帝的意思。
诗人,一点点恶败,就完了,俗了,一句好诗也写不出来。
诗真是有神的。一俗,诗神就什么也不给你。


